【历史文化】古代考绩制度的成与败‖杜君立
古代考绩制度的成与败
杜君立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将现代社会称为“绩效社会”,绩效几乎成为现代管理的精神核心。事实上,现代社会完全是古代社会的延伸,正如工业是农业的延续一样,现代白领守着电脑工作,与工业革命时期工人守着机器、农耕社会农民守着庄稼、牧人守着牛羊是一样的道理,都遵循一样的利益与效率法则。
中国古代社会拥有当时最成熟和最为完善的官僚制度,如果说古代皇帝是想用最小的成本来获得最大的收益,那么官僚体系就是其最大的成本付出,对官吏的绩效考核不仅事关皇权的收益,甚至还决定着皇权统治的安全和成败。正因为如此,政绩考核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很早就有,而且一直很受重视,这不仅体现在历朝历代的法律法规中,还形成无数历史文献记录。在古代,对官吏政绩考核一般称为考绩、考课、考功等,本文统称考绩。
“上计”制度形成于汉朝

科举制度改写了传统官僚体系,由吏部专掌官吏之考课。
尧舜禹是中国历史上远古的圣君,因为贤明善政,留下一个“三代之治”的历史典故。作为“四书五经”之一的《尚书》记录了很多舜帝的言行和事迹。《尚书》的《舜典》中就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庶熙”之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每隔三年就要考核一次官员政绩。经过考绩,凡是有功绩的人便给予升官,反过来,有过错的就要被罢官。
在《尚书》的《立政》中,记载了夏朝的“三宅”和商朝的“三宅三俊”。所谓“三宅”,指的是常伯、常任、准人三种官职,所谓“三俊”指的是刚克、柔克、正直三种品德,都与官吏考绩有关。到周朝建立,有了更加明确的考绩意识。
由春秋到战国,法家兴起,变周制为秦制,关于官吏考绩进一步走向制度化和常规化,这在现代出土的秦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汉承秦制,使考绩制度进一步走向完整和完善。
汉朝由刘邦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平民统治,终结了贵族传统。汉朝创建之初,便重用儒生叔孙通,在强化儒家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大力加强皇帝集权的中央统治。具体来说,一是在秦制的基础上,对丞相权力进行分解,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三公下又设九卿;其次,不仅对地方官吏进行考绩,而且连丞相三公也不能例外,尤其是东汉时期,对三公的考绩更加严格。
司马迁《史记》中记载,西汉孝文皇帝刚刚登基,在朝堂上向右丞相周勃询问国家之事。皇帝问:“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说:“不知。”又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周勃又谢不知,汗出背,愧不能对。于是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这些都有人知道。”皇帝问是谁,陈平回答:“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廷尉主掌司法平狱,治粟内史主抓钱谷金帛诸货币,都是位列九卿的重要官吏。
汉朝的考绩称为考课,其最典型的体现或许是在汉武帝时期。当时发动了对匈奴的连年战争,每次战争都会对参战将士进行详细严格的考绩,胜者有功得赏,失利者受审受罚。
按照汉代考课制度,中央对郡以下的常课主要由丞相和御史大夫负责,有时皇帝也会亲自主持。每年年底,各个郡国守相都要汇报一年来的工作成果,主要内容包括户口增减、垦田农桑、漕运水利、钱谷出入、盗贼狱讼、教育选举、灾害疾疫等。各地提交给上级的考绩报告称为“上计”。
为了核实“上计”内容的真实情况,汉朝又设立了用于监察的刺史。
汉代很多政治制度都是由汉武帝建立的,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共设十三个刺史,按是否犯有聚敛为奸、刻暴杀人、蔽贤笕顽、放纵子弟、勾结豪强等行为,来刺察各地长官的治理情况。对于守法者各有升赏,违犯者则要受到弹劾和处罚,严重违法者甚至会被撤职罢官乃至刑罚。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有一篇《考功名》,详细记录了汉代官吏的考绩制度,考绩原则是“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具体考绩分为九等,从上上、上中,而至下中、下下,以这九等来确定考绩合格程度,从而确定奖罚措施。在汉元帝时,京房向皇帝提案了一套完整的“考功课吏法”,受到皇帝的嘉奖。
汉代以察举、征辟来选官,这种制度重德轻才,以道德为第一要务,但道德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此属于典型的“人治”。魏晋以后改为九品中正制,比较注重才干,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董仲舒的九等考绩法。
汉王朝崩溃之后,从三国、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末,中国社会长时间处于四分五裂且兵荒马乱的状态。这一时期门阀势力炙手可热,考绩制度难以实行,但出现了著名的“月旦评”现象,充分发挥社会舆论(“乡论”)的力量,让很多官吏都感到敬畏,自我检点,“莫不改操饰行”。
考绩制度趋于繁复
李唐王朝建立之后,以文章辞赋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重新改写了传统官僚体系,作为六部之首吏部有考功郎中和考功员外郎,专门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
因为安史之乱的原因,唐玄宗和李林甫被视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和奸相,但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由唐玄宗和李林甫等人编撰的《大唐六典》则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官制的开山法典。《大唐六典》中对考绩有详细记载。唐代考绩的具体安排是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对具体的考绩内容也都有具体的规定,即“四善二十七最”。
所谓“四善”,即“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所谓“二十七最”,指的是不同职能部门的理想标准,如“铨衡人物,翟进贤良,为选司之最”,“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等等。按九等考分,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二善为中上,无最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事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缺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
《大唐六典》出现于安史之乱前的太平盛世,体现了官僚制度最理想的治理状态,但不久爆发的安史之乱将中国重新带回到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经历五代十国之后,到宋(辽金)时代,社会才重新安定下来。
宋代基本延续了唐代官制,不仅科举制度非常成熟,相应的考课制度也更加细化。然而,宋代官僚制度严重内卷,这不仅导致冗官泛滥和叠床架屋的繁文缛节,也让各种制度在具体实施中流于形式,不能产生实际意义。更有甚者,官场激烈的内斗让考课沦为党同伐异的借口和工具。
在中国所有王朝中,元代疆域很大,但国祚很短,在制度建设上更是乏善可陈,甚至一度废弃了科举制度。到了第四代皇帝仁宗时(1311—1320年),不仅恢复了科举制度,还出台详细的官吏考课制度,号称内容包括“三要、九征、二十六美之三十九类”。
所谓三要者,一曰公,二曰廉,三曰勤。所谓九征者,一曰远使之而观其忠,二曰近使之而观其敬,等等。所谓二十六美之三十九类,更是博士买驴一般毫无用处的长篇大论。
仁宗曾问右丞相阿散:“卿日行何事?”对曰:“臣等奉行诏旨而已。”仁宗说:“祖宗遣训,朝廷大法,卿辈犹不遵守,况朕之诏旨乎。”然而实际上,仁宗也受制于太后,他宠幸的臣子为非作歹,却对此视而不见。有君而无臣,让人一叹。
从宋元到明清,中国官僚政治逐渐到达了一个极度完善的程度,尤其明清两代,几乎堪称古代中国的历史巅峰。按照明朝的百官考绩法,三年为一考,三考为满,考满之后分等级,即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合计九年三考总评来定升降奖罚。清朝将考绩标准定为四格八法 。“四格”即守、政、才、年,每格分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八法”为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后去掉贪、酷,改为“六法”。清代对地方官的考绩称为“上计”,每三年一次,由州、县至府、道、司,层层考察,造册上报督抚,再由督抚核其事状,注名考语,缮册送吏部复核。
明代还要求在京外的地方官每三年一次进京接受考察,称为“朝觐”。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亲自考核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117名府州县官吏,其中称职者占十分之一,不称职者十分之一,平常者占十分之七,昏庸贪污者十分之一。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
人常说宦海沉浮,仕途坎坷,自古官场都是尔虞我诈,竞争激烈。按照明朝铨选制度,官吏升迁必须经过考选、保举、考满三关。那些与达官权贵同党者,可以轻易过关腾达;而很多官员才识过人,却长居人下,只因朝中无人。明代许多“在内御史、在外知县、知府,往往九年不迁”。
明代有完善的监察制度,科官监察六部,道官监察地方,但科道官都陷入党争。在某种程度上,科道官决定了官场构成,而科道官的任免又掌握在朋党手中。明代中后期,科道官的升陟降黜,不在于个人政绩,而取决于党派势力。朋党的用人之道是“所爱者不肖必留,所憎者虽贤必去”。严嵩掌权时,视不附己的科道官为眼中钉,利用京察之便徇私报复。如嘉靖三十年(1551年)京察,共有40名科道官被罢调。
事过则损,古代考绩制度的失能

在皇权体制下的考绩机构往往徒有其表,难以落实执行。
一部考绩史,也是古代中国的官吏绩效考核史。
从专门的法律法规到专门的考绩机构,从秦灭六国直到晚清废除科举和宪政改革,中国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对官员的监督与考绩。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有吏部考功司、宋代有审官院、考课院和监司,明清两代有吏部尚书和御史台、督御史等。但这一切都建立在存在严重缺陷的皇权体制之下,很多考绩机构徒有其表,很多考绩政策流于形式,徒具形文,难以落实执行。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论私不论公,古代官场更是重人情轻法治,如同宗、同乡、同寅、同年、同门、姻亲等,各种裙带关系盘根错节,因而徇私舞弊,官官相护,上下串通。“至堂考核司属,朝夕同事,孰肯破情面至公,其中钻营奔竞,弊不胜言。”(《清朝文献通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官场的朋党现象极其盛行,结党营私,常常借考绩之名行党同伐异之事。在权力游戏中,下级官吏的升降荣辱完全取决于上司长官,而不在于个人政绩的优劣。为了保住禄位和求得仕途通达,下级官员必须利用一切机会逢迎献媚,贿赂钱财,死心投靠,朋比为奸,才能“越俸升转”。
从程序上来说,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也不可能事必躬亲,虽然也有回避制度,对官吏群体的考绩过程本身就属于暗箱操作,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这些都是古代绩效考核制度无法达到应有效果的根本原因。
《左传》中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中国每个王朝初立,百废待兴,往往富有朝气,会制定比较好的制度,依靠清明的官场风气,营造出一个所谓的盛世;慢慢的,权力日益内卷腐化,各种制度被束之高阁,万事俱废。比如在唐朝后半期,地方上藩镇林立,朝廷又沉沦于牛李党争;在明朝后半期,皇帝昏庸,宦官厂卫与文官集团残酷斗争,吏治江河日下;清朝后半期内忧外患,满汉相疑,不同利益集团势不两立,坐看鸦片泛滥成灾,民不聊生。
隋朝灭亡后,李世民看到隋炀帝的笔迹,便问魏征:“炀帝讲的都是尧舜之言,何以灭亡?”魏征说:“讲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蒙蔽百姓,鱼肉天下,焉有不亡之理?”李世民叹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古语云:“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正如黄宗羲定律所揭示的,阅读历史便会发现,不管哪个王朝,几乎所有皇帝都口口声声要整顿吏治,但最后都免不了虎头蛇尾、始乱终弃的结局。《唐会要》记载:“自至德(唐肃宗的年号)以来,考绩之司,事多失实,常参官及诸州刺史,未尝分其善恶,悉以‘中上’考褒之。”
回顾明清两代考绩制度,刚开始时确实起到了一些效果,但随着时间推移,很快就百病丛生,最后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无论是“大计”还是“京察”,抑或是“考满”等,在朋比为奸、营私舞弊的官场想要做到“循名责实”,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明代有御史巡按考察地方官吏时,人还未离开京师,送来打招呼、托关系的条子就已经装满口袋。于是到地方考察官员,御史最后揭发弹劾的官员大都是政治上比较单寒孤立之人。“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代时知府、知县等地方官每次考满朝见时,每人至少在京师要花五六千金行贿上司才行,而上司则以下属是否行贿作为奖惩标准,无功者可以用行贿的手段来冒功领赏,有功而不行贿者不仅没有奖赏,甚至还要受到惩罚。
《明史》记载,“神宗(万历)末年,征发频仍,矿税四出,海内骚然烦费,都县不克修举厥职。而庙堂考课,一切以虚文从事,不复加意循良之选”。《清实录》记载,康熙初,有御史批评考绩虚应作假,康熙也承认:“考满之典,原欲分别贤否,以示惩动。近因内外文武各衙门,考核各官,多系优等,劣等甚少。各官徇情钻营等弊,且章奏繁扰,实于劝惩无裨。”《清史稿·考绩》记载:“乾隆末,士夫习为谄谀,堂官拔识司员,率以逢迎巧捷为晓事,察典懈驰。”
来源:官察室
作者:杜君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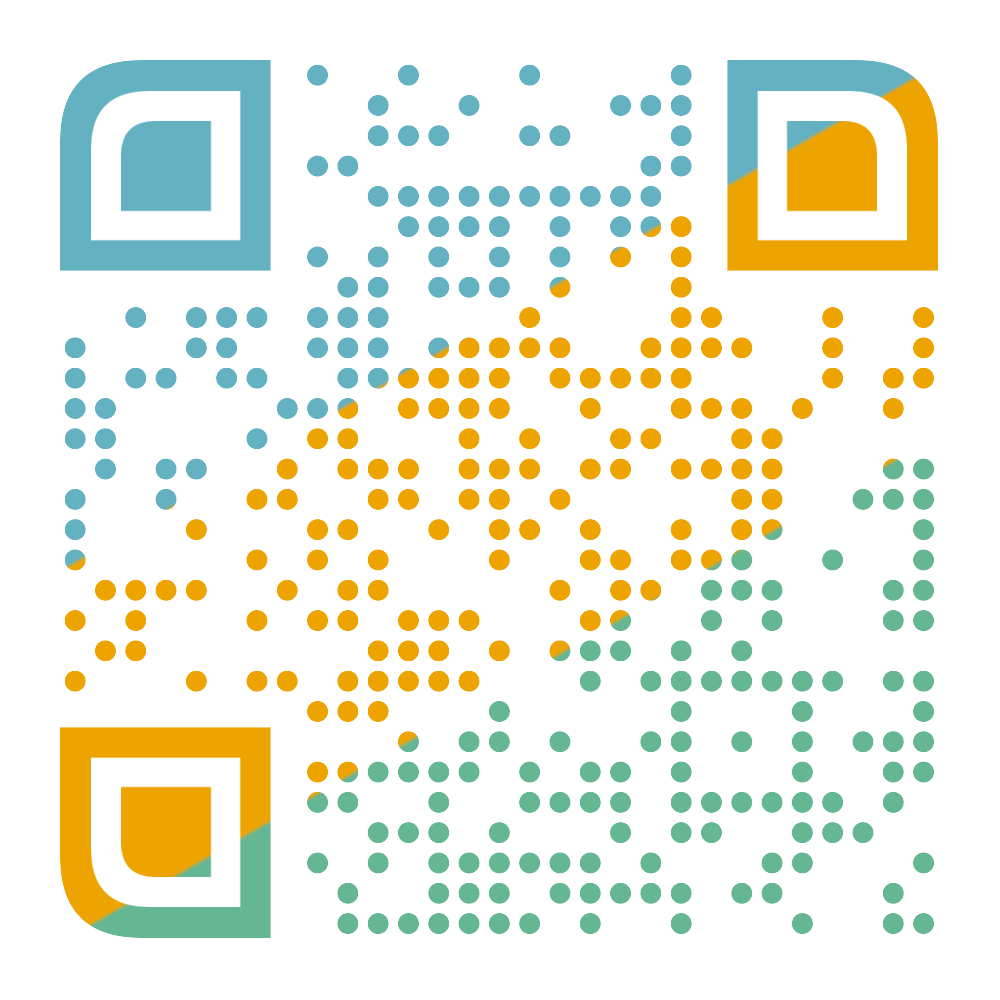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