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文化】看望慈母‖伍锋
看望慈母
伍 锋
四九的第五天,天气奇寒。五十年未遇的雪冻,没有阻挡住我南下的信念。登上南去的大巴,天上纷纷扬扬飞舞着如银雪花,两边绵延的群山,拔地而起的高楼,还有泛着波光的河水,以及绿油的麦苗和油菜,都唤不起我内心任何的联想,因为我的心早已飞到故乡,飞到了慈母身旁,一切的思绪,都静静地驻步在阎维文的那首催人泪下的《母亲》上。

劳动归来的母亲
平时每每想到母亲,我就打开电脑,登上我的51博客网站,然后在“音乐”栏中点开由阎维文演唱的《母亲》。听到阎维文优美动听的演唱,所有的心都随着歌词的内容,一步一步地滚动。这时,母亲昔日为我煮饭、洗衣、缝书包、扎鞋底的情境,便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在竹篮里睡得正香,父母亲都出门了,哥哥们也出去了,我们队上一个姓曾的疯子上前紧紧地卡着我的脖子。我突然醒了,只感到呼吸十分困难,脖子疼痛,心里十分难受。正在这时,回家看望我的母亲突然看到这一幕,立即拿起家中的扫把,迅速向疯子打去。疯子见母亲打来,放开手,马上跑走了,我的命也得救了。
我上师范时,学校生活实在太艰苦,每次回到家,母亲总要想方设法给我煮上我最爱吃的糯米馍加肉片的连锅面。过年时,母亲总是先炖好猪脚、猪肉和鸡肉,新年的第一天,她又第一个起床,给我们弟兄六人热上前一天的好菜,摆好筷子和碗,给每个人准备好热酒,然后静静地等待我们起床(我们家的习惯是大初一不喊人起床)。
每次我离开家前,母亲还要给我准备一大包煮熟了的鲜鸡蛋和精瘦肉等不少好吃的东西,并千叮咛万嘱咐,叫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生病了。
当我踏上求学之路时,母亲总要满眼噙含着泪花,把我送得很远很远…目光中全是祝福和期盼。

母亲晚年在攀枝花
后来我参加工作了,母亲总还牵挂着我。我在朝天区委当秘书时,曾把母亲接到身边,心想让她老人家享享福,报报她老人家的养育之恩,可是我每次从家中走出后,母亲就从家中走出来,身体依偎在我上班路上的那条巷子的墙边,久久地注视我上班的方向,完全不回家,直到我下班回来,母亲才拉着我的手,满脸微笑地同我一同回家。那时,我完全不能明白母亲此举的意思,还曾轻轻地责怪过母亲,但母亲总是以微笑回答着。
后来,我成家了,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每次我回家,母亲又多了不少关心的内容,总是关切地问候我、我爱人和我女儿的情况。记得1996年,我在朝天区坐火车出车祸,我对远在故乡的母亲只字未提,但到第二天下午,三哥受母亲委托,还是给我打来了电话。母亲说她做了一个梦,应在我头上,说我有可能出事了。也许是母子心灵感应,母亲的感觉毫厘不爽。尽管我说没有什么事了,但母亲仍牵肠挂肚,不时还打来慰问电话。
想到母亲不仅给了我生命,还给了我这么多浓浓的母爱,坐在电脑前,我的泪水就禁不住潸然而下。回到家,妻子不明就里,以为是电脑伤了我的眼睛,总是叫我少用电脑。我没有多说什么,只让泪水悄悄地从我的眼中流到心中……
车到绵阳,已是中午,我把将要参加高考的女儿送到学校,匆匆忙忙地泡了一碗女儿为我准备的方便面,边吃边向公交车站方向走去,然后直赴南湖长途客运车站。好不容易捱到下午两点三十二分,全车人员到齐后,车子才缓缓起动。车子在绵阳至大英的路上飞奔,但我总觉得司机开得太慢,不时还在催促。下午五点三十五分到达大英,我马上与三哥取得联系,然后草草地买了点水果糖和祭奠父亲的香、蜡、火纸,又直奔大英车站。
坐在大英到象山的公交车上,司机不守诚信,把我们拉出站后,在原来叫万福桥的地方就不开了,说是等人。约莫拖延了近一个小时,又说是要买一个汽车配件,把我们又拉回到大英车站。我急于想看到母亲,在车上对司机进行了严厉批评,司机没有回答什么,然后叫全车人员又改乘另一辆公共车,这才慢慢悠悠地把我们向目的地送去。晚上七点左右,我才到达团结乡五大队小沟的分岔路口,三哥已等不及了,正准备往回走。见从车上下来一人,三哥在对面大声地喊了一声“五兄弟”。听到我的回应声,三哥又折转身,给我送来长水靴。
从三哥处得知,家乡今年遭遇50年未遇的大雪冰冻天灾,每天上午天上下着雨夹小雪,下午下着小雨,历时超过半个月,乡村的道路一片泥泞。
三哥从我手中接过我的随身行囊,在前边引路,我空手在后面高一脚矮一脚地紧跟着。冬日的天黑得早,我们兄弟俩只好摸黑回家。绵阳到大英的大巴上没有发山泉水,在大英时因太忙又没有顾得上买水,回到三哥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又冷又饿,又渴又累,疲惫至极。三哥准备给我煮点吃的,我知母亲现在正在大哥处,便顾不上这些,催着三哥直接赶赴大哥处。

喜悦的母亲
来到大哥家,大哥大嫂得知我回来了,忙来打着招呼。我一边回应着,一边快步奔向母亲居住的房屋。母亲一个人住在大哥家正堂屋左边的那间屋子里。我来到床前,母亲正头北脚南地侧睡在床上。我双手一把握住母亲的左手,口里说着,“妈,我回来看您来了!”母亲回过头,望着我,眼泪像泉水一般不住地往外涌,我的泪水也禁不住涌了出来。大哥大嫂在一旁说着:“妈,这是您的五儿子回来看您了,您不是平时老在挂念吗?您就高兴些吧!”我没有说什么,只是让自己泪水不停地从脸颊上滚落下来。
平时一般情况下,我是从不当着母亲的面流泪的。三哥、大哥和大嫂见我太过难受,相继走出了母亲居住的屋子,大哥去给我煮面去了。我继续握着母亲的手。母亲的手已经干枯得只剩下几根光骨头,血管里的血液似乎也不充盈,头上戴着我两年前给她买的毛线帽子,帽子覆盖着满头的银发,身上穿着弟弟给她买的棉袄以及很多衣服,额头和脸上布满皱纹和老年黑斑,母亲80多年的岁月沧桑展示无遗,青年时期水汪汪的眼睛已经变得白里透着昏沉。母亲神情呆滞,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只是用涌着泪水的眼睛久久地注视着我。
透过母亲的泪水、目光和神情,我知道母亲此时最想听到什么。于是,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对母亲说:“妈,您老人家放心吧!您百年以后(家乡对亲人去世的避讳说法),您生前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们全满足您:不火化,给您做道场,给您请人念经,给您做一个与父亲同样大的灵房子。我向您保证:一定做到!您老人家现在就安心地保养身体吧!”我一边说着,一边用卫生纸给母亲擦去眼中、脸上的泪水。听到我说的话,母亲的心情明显平静了许多,渐渐地止住了泪水。
这时,我才仔细地观察母亲居住的环境。在这个一楼一底的混凝土砖房里,母亲住在一楼最左一间。为了挡寒,窗子严严实实地封着,只有通向堂屋的门开着。母亲睡的床,紧紧地靠在右边的墙壁边,床前靠右边的前方,放着一个陈旧而又略带赭色的老式柜子,这是母亲当年的一件陪嫁品。柜子里放着母亲的药,显得空空的。床上铺着厚厚一层稻草,稻草上放着一床棉絮,棉絮上铺了一张较厚的塑料,塑料上铺设着大哥为母亲准备的各种衣裤,母亲就睡在衣裤上面。母亲的身上盖着厚厚的一床半成新棉絮套装的铺盖。床的后面,斜放着一个打谷子的拌桶,床的左边,无序地放着一辆旧自行车和一辆俗称“狗驴子”的旧摩托,床的左后方到床的前方,斜拉着一根绳,上面挂满了母亲尿湿的各种衣裤。昨年盛夏后,母亲就失去了行走能力,长期躺在床上,随后不久,大小便也失禁了,由三哥和大哥轮流照看着。今年夏天后,母亲的身体素质再次下降,话也不能说了,饭量也逐渐减少,最后连饭也不能自己吃了,全靠大哥、大嫂和三哥、三嫂给母亲喂。母亲现在每顿还能坚持吃一至二袋维维豆奶,比一个半月前弟弟回家看望时的情形略微好些。母亲睡的床前,悬空挂着一个大约只有25瓦的灯泡,除了她可以依赖的儿子外,这个灯泡和那扇可以转动的门,就是母亲眼前和心中的全部光明了。看到这些情境,我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难言与难受和心痛。

三哥照料母亲(摄于2007年春节)
我赶忙从我的包中取出为母亲买的氨基酸口服液,给母亲喂,可母亲的嘴难以张开,大哥从柜子里的药箱中,取出一个注射器,从氨基酸口服液的瓶子中汲取了满满一管氨基酸液体,然后取下针头,从母亲微微张开的嘴边注射到口中。过了一会儿,我又给母亲喂了一片钙片和六颗速效救心丸。等了一会儿,大哥给母亲兑好了一碗豆奶粉,一勺子一勺子地给母亲喂。看到这些,想到儿时母亲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爱,我的泪水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迅速转过身,快步走到大门边,眼睛望着飞着小雪下着小雨的蒙蒙苍天……
母亲白天大多睡觉,晚上呻吟。每隔一个小时左右,或母亲每次呻吟,大哥都要去看望一次,把屙湿了的衣服换掉。母亲瘫痪一年多,后背和两个臀部都睡烂了,身上也有一股明显的臭味,每天晚上睡觉前,大哥都要给母亲喂一次止痛的药,并给溃烂的地方敷上去痛生肉的药。
每天母亲醒来时,我尽量陪着母亲,跟她说话,母亲不能说什么了,但我知道母亲心里一定十分明白,我更相信母亲能完全听清我的话,我坚持每天给母亲喂氨基酸口服液、钙片和速效救心丸,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母亲床前问安,给母亲洗脸,晚上睡觉前再看望一次母亲,向母亲作一天的小小告别。
到家的第三天,是三哥给我接风。三哥一大早就从家中来到大哥处,告诉大哥中午不要煮饭,全部到他家吃午饭。说罢,他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故乡的小雪小雨中了。
没过多久,母亲就开始呻吟,大哥熟练地走到母亲床边,揭开铺盖一看,一股大便的气味立即从母亲的臀部下飘了出来。大哥麻利地拿来换用的衣服,先给母亲擦拭干净,再把母亲抱起移开,重新铺上待用的衣服,又把母亲放回原处。母亲没有再呻吟了。大哥这时拿着有屎的衣服和一个高粱刷子,走到水池边,一边来回在水中甩动着衣服,一边用高粱刷不停地清刷着母亲的大便。衣服上没有明显的大便后,大哥又拿着母亲的衣服放到房前水沟外面的青石板上,然后端过来一盆清水,拿了一袋洗衣粉和另外一把洗衣刷子,走到青石板前,一边向衣服上撒放着洗衣粉,一边用刷子使劲地洗刷着。
我想到平时大哥和三哥照顾母亲异常辛苦,便抢着去洗。“大哥,平时您和三哥照顾妈很辛苦,今天就让我来洗吧!”“不了,兄弟,你们在外面工作也很辛苦,还是我洗!”大哥终究没有让我给母亲洗屎布。我急忙从大哥家的水缸中提来一桶清水,放到大哥身边。天上的小雨和小雪继续下着,小雪落到六十二岁大哥的头上,我分不清是大哥的白发还是天上飘下的雪花。冷风和雨雪中,大哥的脸、手、鼻都冻得乌里透红,脸上却洋溢着微笑,洋溢着对慈母天恩的报答,洋溢着一份浓浓的弟兄情。
再过三天,母亲就将要到56岁的三哥家,由三哥照顾一段时间。三哥从小多病,身体单薄弱小,却勇于承担照料老人的责任。20年前曾照料过父亲现在又与大哥携手照料母亲的三哥,很善于总结,有着十分丰富的照顾老人的经验。想到大哥和三哥有时不得不放下做农活和收购废品挣钱的机会,就这样辛勤地轮流照顾着母亲,想到母亲晚年的如此境况,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回家的前三个晚上,我住在大哥家,一是为着照看母亲,二是想对大哥多一些安抚。离家的头一天晚上,我住宿在三哥家。我虽然不能像大哥三哥一样更多地照料母亲,但我在离家前一定要做好有关方面的协调工作,这是我回家前的计划。
离开家乡前一天的傍晚,我向母亲辞行。外面天色朦胧,小雨照旧淅淅沥沥地下着,屋内灯光暗淡。听说我要准备走了,母亲仍然躺在床上,没有说出半句话,眼泪从眼角又流出来了。我看得出母亲的难受,其实我心里更难受。说句真心话,只要上苍同意,我真的愿意把自己护送女儿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所有属于我的年岁和幸福,都送给我亲爱的母亲——只要她老人家还能健步如飞,只要她老人家晚年幸福,只要她老人家不再遭受瘫痪的折磨!——我一定要尽到为人之子和为人之父的双重责任!

笔者最后一次见到的卧床中的母亲
告别母亲,我毅然向我工作的方向走去,泪水挂在面颊,祝福长驻心间。我必须努力向前,不管前方是荆棘丛生,还是布满风霜刀剑,不管多么坎坷,也不管多么漫长,拥有母亲给我的希望,拥有母亲给我的信念,拥有母亲给我的力量,拥有母亲给我的智慧,我一定会变得更加坚强,泪水会变成美丽的花朵,久久地在人世间绽放出别样的芬芳!
这时,阎维文唱的那首《母亲》的歌,又在我的耳边萦绕,悠扬婉转,不断地向四周传播,向我的心灵底层渗透,两股热乎乎的泪水好似小小的瀑布一般挂在我的脸上……
补记:本文于2008年2月2日写就,1个月后母亲与世长辞。这次看望母亲,成了我与母亲的最后一见。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伍 锋(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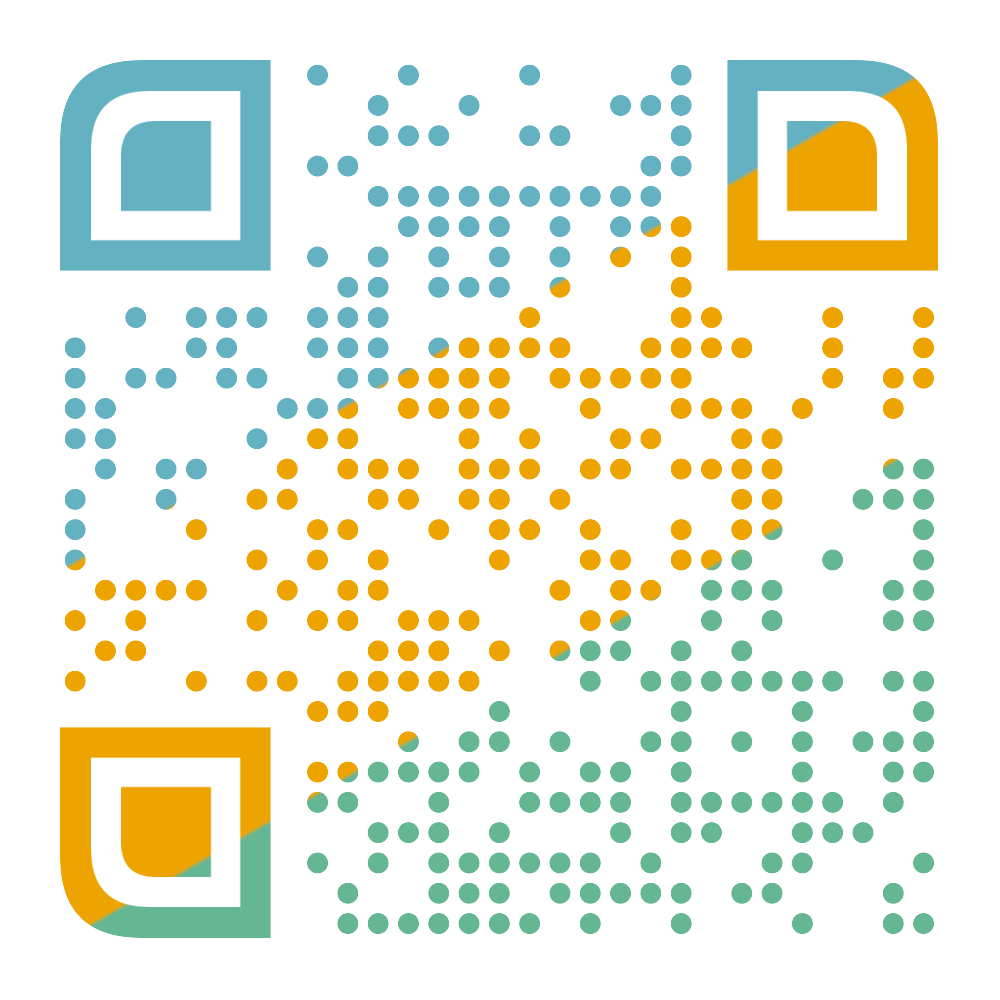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