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时间的履痕——从物候历到铯原子钟‖黄森
时间的履痕
从物候历到铯原子钟
黄 森
从物理视角看,时间是为度量物质运动和变化过程而人为设定的参照标尺。就此定义而言,这只是基于现代认知条件下的评判,大体不能涵盖时间这一概念的原始属性。站在华夏视角,结合帛书版《道德经》所言“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华夏先民用了大约万年来探寻自然法则,尤其是对天文运动规律的探究,所获取的知识成果,即古人所称“天道”,通常能顺畅施用一时,但并不能保持恒久,总会随着精度需求和测量手段的提高,而被后世修正;同样,人们对某一事物的定义,在其定义形成的那一刻,便注定不周全、不精准,总会在日后的某个时刻得到补正完善。
鉴于此,是否可以认为,人们对“时间”这一概念的定义一直是持续更易的,现代人习以为常的时间标识体系,也是经过上万年的精度累进以及在无数次试错中不断修正而建立起来的。这让我们能够看到,度量时间的方式演化所串起的历史印痕。
一
先问一个有趣的问题:原始人类知道一年有多少天么?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就像公路上的里程碑,没有公路,何来里程之说?同样,没有时间观念,哪来计时系统?在他们意识里,甚至都还没有“年”这个概念,至于一年有多少天,更是不知何从谈起。
这反而让我们更加想去了解,原始先民对自然环境往复变化的精准识别,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以想象,懵懂的远古人类大约是不会有空间和时间概念的,这或许便是后人所说的“混沌状态”。就像山中猴群对各种野果的成熟时间有着比较敏感的反应,但这只是一种天然的由生存欲望引发的原意识,并不意味着野猴对于时节更替有了具象的感知。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总归有一名远古先祖,从俯仰观察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定义出“天”与“地”这对概念来,不知这是否就是后人理解的“开天辟地”。这首先是个空间概念,继而在空间的交互和场景的转换过程中,才赋予了其时间属性。换句话说,有了天地这个空间,才有了天地互动产生的时间观念。相较于不知方位、不晓时日的原始混沌状态,这在人类繁衍的历程中,必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或许在历史上的某个节点,有一位或多位远古先民,在生存需求与好奇心的共同驱使下,用TA那并不发达的大脑,试图去理解黑暗与光明交替往来的缘由,去记录周遭的植物从绿变黄的枯荣过程,去解析花开叶落、果实成熟与日升月沉、寒来暑往的关联性。自此,时间的雏形萌生。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华夏语境里,“时间”的原生状态。当华夏原始先祖们逐渐步出混沌,开始以粗陋的方法去标定时节,以应对狩猎、采集的丰贫变化问题,或是解决牧牛、放羊时的草木枯荣问题,以及种植稻粟等农作物的播种、收获时机问题,便有了时间产生的现实逻辑。这显然是生存欲望驱使的,具有极强的功用性,而不是单纯为了搞理论研究、写写论文对吧。
基于此认识,我们试着从解析汉字“年”的构造逻辑入手。甲骨文的“年”字,有着一株禾苗的典型状貌,《说文解字》谓:“年,谷熟也”。由此可否认为,年这个时间段落,早初就是为度量禾苗的生长周期而产生的?或者说,对于华夏先民而言,时间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标示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完整过程,以期精准管控生产行为而提高粮食产出。
按这个思路,我们再来看看“历”字,其字源为“厤”,后又衍生出“歷”和“曆”。望文而生义,二字核心都在“秝”字上,或许造字本意皆与农作物有关,但其区别在于:“歷”字下面为止字,代表脚掌的形象,着重描述参与某件事的过程,指的更多是一种经历;而“曆”字下面为日字,即太阳形象,侧重于表达对农作物田间管理的时间节点控制,可以理解为通过度量农作物生长周期,以实现精细化过程管控的一种行为。顾名思义,“曆法”便是实施这种行为的具体方法。当然,无论从字面上怎么去解读,伴生于农业耕作的历法,其本初意义都是为农事生产提供时间参照标尺。但今天对于历法的定义,其内核显然偏向于计时系统,而脱离了最初的指向。
二
自打有了“年”这个概念,远古先民们就能准确掌握节候轮转的规律了么?显然不能,早初的“年”只是一个表示周期的大致概念,虽给出了一个区间范围,但其边界是模糊的,并没有一个精确的指示数值。
这里,我们先做个情景实验。假如您是1万年前的一位农夫,您怎么来度量季节变化,并标注时节的更替,以确保播种、收割不误农时?
您可能会先标定一个点,比如以家门口的柳树抽出嫩芽这一事件为基准,观察柳树叶历经青翠,再到枯黄,继而飘落,又被冰雪覆盖后,直到下一次抽芽,形成一个循环。于是,您将这个完整的循环过程定义为“一年”。在这个周期内,您使用一定的记录方法,以一个昼夜为最小单元,将其计为一天,再统计总的天数。或因各个部族计数习惯不同,目前已知上古时期记录方法有结绳、垒石、推策(翻竹片)、刻木等,不一而足。
由于单一物体变化历程漫长,其参照价值和可靠性不足,标定点也不紧凑,加之每个周期都会出现偏差,于是您想到,用多种标定物形成参照系统。您会利用身边的各类事物,形成一组参照点,并用以指导农事,比如看到蒿子花开,就要开始翻地;听到布谷鸟叫,意味着即将播种;看到树叶枯黄,预示着准备收割庄稼……以及通过观察动物的蛰伏、候鸟的往返、降水的多寡、气温的升降等来确定时节。然后,将每五天划为一个时段,用一种事物作为参照标定下来,称作一候,再将这些标定点串联起来,便形成了最原始的历法。
除了以实物的变化作为季节参照,华夏先民还发明了一种标注时节的方法,叫“候风法”,也称“相风法”,就是通过观测风向的变化来推算时节的更易。比如以黄河中下游为代表的季风气候区域,若观测到东南风刮起,预示着雨季即将来临,便到了播撒种子的时候。因此,古人将风向与时节基本绑定起来,后来又形成了一个概念:“八方风”。《淮南子·天文训》里将八方风作了一定阐释,后《说文解字》作出完整、系统的解读:“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闾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也就是把八个方向的风基本对应到春、夏、秋、冬四季之中。有学者提出,候风历法与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有内在关联,但尚需考证。
以实物参照的方法与候风法,共同组成了物候历法,它包含了温度、风向、降水量变化,以及动植物生长周期等多种元素,比如“东风解”“桃始华”“鹃始鸣”“蛰虫伏”等显性现象。但是,由于受环境气候等波动影响,物候历偏差会很大,准确度低,有较强的局限性。于是,华夏先民又将目光投向天空,试图以日月星辰运行过程中的相对位置作为参照系,来标定时节的变化。《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至此,物候历法失去主角光环,而华夏历法开始与天体运动深度绑定。当然,由于普通老百姓对天文知之甚少,物候历法与天文历法在时间轴线上一直长期并行和交叠,也就是说,自天文历法出现后,物候历仍作为考量时节变化的工具之一,并融入后来创立的二十四节气中延续下来。成书于约3000年前的《夏小正》,便记载了数千年总结下来的物候、气象、农事等诸多经验供百姓鉴用。
现在,我们来看看天上都有些什么:有一个很大很亮还能发热的火团,古人将其取名太阳;有一个很大且明暗周期变化的圆盘,唤作月亮;还有几颗持续行走的小星星,叫作行星;以及密密麻麻的看上去位置基本恒定不动的星星,名为恒星。那么,这些又跟季节变化有什么关联呢?华夏先民通过长期观测,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循环往复的规律,也就是太阳、月亮和恒星等在天空中的视运动引起的周期现象。我们知道,这是由地球绕着地轴旋转引起的,但先民们显然没有这样的认知,他们只知道在“天道左旋、地道右旋”在轮转中,四季也随之更替。
最初,华夏先民发现在一年之中太阳升起的位置是不断变化又遵循着某一周期性规律的。于是,某位聪明的古人想到,利用家附近并列于太阳升起方向的五座山峰作为参照系(或许“列山氏”之称便来源于此),选取一个固定位置作为观测点来观察变化:比如,当初升的太阳处于最右边山巅的某个点位,这时感觉太阳最远,这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冬至,即太阳从南回归线返回的节点;同样,当太阳从最左边的山峰的某个位置升起时,即是从北回归线开始南移的夏至;当太阳处于中间山峰某个固定点时,形成了春分、秋分的雏形;以及太阳从第二、第四座山峰爬上来时,分别代表后来定义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节气。尤其四时的确立成为天文历法系统的基石,这在《山海经》和子弹库帛书里都有提及。
这种测量太阳回归运动的方法叫作“归藏”,开始于“二分二至”的确立。文史学者黄饮冰认为,古人对太阳回归年的基础分节是“四时四节”,这就是原始的衡间理论“三衡两间”(“三衡”可理解为南北回归线与赤道,“两间”即三条线之中的区间,这在大地湾文化陶器、马家窑文化彩陶上都有所体现)。后来,这一方法延伸为“四时八节”,便称为“五衡四间”;再扩展为“四时十二节”,就是“七衡六间”。距今7800年到6800年的高庙文化陶器上的八角星,以及距今6800年到6300年的汤家岗文化陶器上的八角星,均指向“四时八节”之意。
为提高准确度,古人又辅以日落方向的山峰用以参照,跟日出方向的山峰一一对应(我们熟知的“连山”一词或许便由此而来)。同时,古人还引入了月亮运行轨迹作校正,这或许便是《山海经》中所言“日月出入之山”,也可能是大汶口大口尊刻符所描绘的场景。
大约在山峰定位方法推广和提升的过程中,又衍生出两种形态,一种是由距今4000多年前的陶寺都邑呈现的,通过夯土观测柱间的缝隙测定太阳位置来确定时节的方法,这比起观看太阳从山巅升起的大概位置,显然精确多了。这一系统可能持续使用了数百年之久,直至因地轴晃动产生的累积误差,导致观测柱缝隙与阳光的投影角度之间发生明显位移,而不得不被弃用,毕竟当时的司天者还不知有“岁差”这一概念。但这种方法只适合于具有一定规模的观测平台,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撑,而这些资源,大概只有帝王才能调度。
如果您只是一介平民,没有那么雄厚的物质条件,却有着十足的好奇心,又拿什么去观测太阳的位置关系呢?聪明的您想到,何不用一具树状物,以“树丫枝”来替代五座山峰?您先选取一根粗实的木棍作为基杆,再在顶端安装上五根木条,呈发散状高低排列,以模仿五座山峰。在使用过程中,您不断比对和校正,以适配观察到的呈斜“8”字形的太阳往复运动轨迹。相对于陶寺夯土柱观测平台,这种树状物便于携带,不会受地理条件限制,只需将观测点位置相对固定即可。您将其称为扶桑木,并在使用中不断修正完善。为了增强其精确性,您还用另一具树状物来观测太阳落山的位置,以作比对,您把它叫作若木,跟扶木形成对应。您将扶木置于日出的方向,将若木安放在日落的方向,于是,扶木与若木便替代了日月出入之山的功能。
在使用扶木观测的过程中,您发现太阳投射到树身产生的影子,也在按一定规律变易。您试着将影子的末端标记下来,经年累月,发现日影在两个标记之间有规律地往复变化。依据这一现象,您将扶桑木进行了改造,撤除了顶端的桠枝,在底端安装了一块带有刻度标识的木板。您将扶木改制的立柱称为“立表”,将带有一条条平行印记的横板命名为“圭尺”,二者合称“圭表”。通过测影,确定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成为推算全年历法的基准点,《尚书·尧典》将其记载为“日中”“日永”“宵中”“日短”。这种方法同样也得到陶寺遗址出土文物印证。
无论用什么方法,对太阳与时节关联性的观测,都离不开辅助工具作为标尺,这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并非易事。那么,有没有更简便直观一些的办法呢?华夏先民又仔细观察夜空。
在夜晚,最显眼的天体当数月亮。要说古人应该很早就留意到这个玉盘的圆缺现象,相对于太阳而言,这个特征无疑是最容易掌握的。但是,月相变化一个周期历时太短,而若干个这样的周期叠加又与太阳回归周期、农作物生产周期无法紧密适配。这主要是因为月相变化除了引发潮汐,以及月亮的引力作用与少数作物根茎水分含量有一定关联外,总体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十分有限。即便不与农业勾连,单纯作为计时系统,月亮运转周期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起居的指导价值也并不高。基于此,可以认为在华夏独成体系的月亮历法似乎很难成立,只有与太阳历法协调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指示作用,而单纯的太阴历只具备原始自然崇拜和宗教意义。
苍龙六宿(后扩展为七宿)应该是华夏古人最早作为历法参照系的恒星组团之一(据传南方部族以朱雀七宿为参照),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的蚌塑龙虎大体能印证这一点。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也延续着这一图腾形象。华夏先民很早就留意到这一组恒星,将其统称为“龙星”,并通过想象,赋予了其“龙”的鲜活形象,划分为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箕宿应为设立二十八宿时添补进龙星的)。由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时,受地轴倾斜影响,苍龙七宿在北半球的可见性会随着视运动而变化。基于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位置,华夏先民春天能够看到龙星从地平线升起,取名“苍龙”或“夔龙”,民谚“二月二,龙抬头”便源于角宿出露;夏天可见龙星处于偏南方向的夜空中,称为“应龙”,大体意思是作物生长需要大量雨水,而龙星能求雨得雨、应许于人;秋天的龙星出现于西方并逐步沉下地平线,唤作“烛龙”,古人觉得其能掌控昼夜变化和寒暑交替;冬天龙星隐藏于地平线下,叫作“相柳”,先民认为其潜于沼泽,易经乾卦爻辞“潜龙勿用”即为此理。就观象授时的寓意而言,“苍龙”启春耕,“应龙”主夏雨,“烛龙”司秋序,“相柳”喻冬藏。
龙星组团中有一颗“大火星”,即“心宿二”,也是西方命名的天蝎座a星。它又被叫作“大辰”“商星”等,就是诗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里的商星。相传帝喾高辛氏封其长子阏伯于商丘,阏伯是帝尧陶唐氏的火正,以火纪时,祭祀大火,所以商人将其称作商星。《左传·襄公九年》:“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天文历法视角看,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即“大火星携日升”,其描述的可能是在商王朝国土上,当太阳初升时,大火星也几乎同时从东方地平线升起的景象。在那个年代,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正好处于春分时节,这是指导农事的绝佳参照物。想必因岁差累积,后来这一现象就“不灵”了,便失去了其指示地位。
再有,就是对北斗星组的辨识。《鹖冠子·环流篇》言:“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就是说,如果在傍晚观测,可以看到二月春分时斗柄指东,五月夏至时斗柄指南,八月秋分时斗柄指西,十一月冬至时斗柄指北。借助斗柄指向地面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可以大体确定四个季节。这些,都容易被普通民众掌握,以便区分时节。
至此,华夏先民初步建立起以太阳、月亮的变化周期为核心,以部分特殊天体为锚点,以行星和众多恒星为参照的天文历法体系,并由此衍生出易经、气象、数学等众多学术。

二十四节气图(钟葵 制图,图源:广州日报客户端)
三
即便有了丰富的观测手段,历法的制定也是一个不断试错、反复修正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将一年这个区间划分为多少个时段,具体划分依据是什么,都在代代转述的过程中早已失真,我们只能通过古籍中的一些模糊的只言片语去揣测,并以当前的科技知识作为工具和标尺,试图还原历史真相、解构历史行为、重建历史过程在历法以及计时系统量化指标的演进历程中,基于太阳回归周期和地球自转周期,可以将年和日定为常量,而年和日以下划分多少个时段,由于没有具体的锚定物,可以认为是变量。
先说对“年”的划分。从一些史料中可看到,上古时期华夏天文历法可能一度出现过将一年划分为十个时段的做法,即陈久金等部分学者所称的“十月太阳历”。虽然这一说法是否真实存在尚待进一步考证,但彝族、哈尼族的确曾长期使用类似的历法体系,而且也有一些佐证指向这种说法。比如,《诗经·豳风·七月》《黄帝内经》中就有“三百六十日”的表述,这可能是指此前模糊地给出的一年区间,或者方便计算而取整为360天。古人将其均分为十个时段,每个时段36天,并将后来发现多出来的5—6天称为“岁余日”用以祭祀(彝族历法称为“过年日”)。其次,华夏先民将一年分为七十二候,规定每候五天,可能也是沿用一年360天的度量习惯,并非一开始就按照365天作计。其三,《山海经》中记录下的日月出入之山是六对,六山之间为五个段落,如每个段落对应太阳北移或南返的各一个时段,合计也是十个时段。再如,陶寺遗址古观象台的观测指向为二十个节气(含“二分二至”),并非二十四个,如果按一年划分十个时段,则一个时段含两个节气,与后来的十二个月对应二十四节气的方式相通。还有,华夏先民将历法投影到圆周上,创立“日行一度”的测绘方法,最初以一年360天对应圆周360度,这一方式沿用至今,后来又将一年精确推算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故《周髀算经》中提到:“何以知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一度?”便是这种方法的延续。
乍看“十月太阳历”这一说法并无不妥,仔细推敲却似有不合理之处:试想月相变化周期平均为29.53天,如若当时一年分十个时段,按360天计每段便有36天(365天计则为36.5天),二者相差甚远,此时古人又怎么会用“月”来作计量单位呢?我们知道,华夏古人最初所称一尺,是以成年男子尺骨的平均长度为基准的;以步为长度单位,是以成年男子左、右脚各向前迈一次为标准。这些,充分说明古人若将一个物事作为计量单位,必定与被计量对象有着强相关性。因此,想来在阴阳合历之前,年以下时段的计量方式不应该是“十月”,而可能是以一年中太阳所处的十个位置为锚点的“十日”(并非后来“十日为一旬”的概念,我们姑且称其为“十日历法”)。
大约在夏商时期,华夏先民先后采用“三年一闰”和“十三月”的方式协调日月周期差异,初步形成我们常说的农历(即阴阳合历),可能这时候才正式使用“月”作为计量单位。至周代制定出19年7闰的办法,终把月相变化周期29.53天与当时掌握的回归年周期365.25天紧密关联起来(由于通常的说法是,一年以365.25天计肇始于春秋,《四分历》颁布于汉代,故只能从结果反推),我们据此作一验算:19年×365.25天=6939.75天;19年×12月=228月,228月+7个闰月=235月,235月×29.53天=6939.55天。至此,回归年周期与朔望月周期寻找到一个误差极小的交合点,这样,普通百姓通过观察月相圆缺变化,就能更容易地掌握节候交替了。汉至隋唐常见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可能描述的就是这一过程,即伏羲代表的阳历与女娲代表的阴历首尾相交。
由此,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干支纪年来源的三种看法:一是说十天干源于前述的“十日历法”,甲、乙、丙、丁等字形皆似种子生长收获不同阶段的状貌;十二地支源于后来出现的“十二月阴阳合历”,子、丑、寅、卯等各代表月亮在一年中的一段行程。第二种说法是,天干源于木星、土星公转位置每十年发生相冲(分别处于太阳两侧)或相合(处于太阳同一侧);地支源于木星一个公转周期为十二年,每一年所走行程即一个地支。还有一种说法源于“极心说”,即以北极星为中心,将天空想象为一口倾斜悬挂于虚无的大钟,所有星体在像钟壁一样的天网上围绕北极星旋转。在北极星后面,有轴绳承系着整个天体,谓之“辛天”,也就是“天外天”(屈原在《天问》里所言“斡维焉系,天极焉加”问的便是这口“大钟”的轴绳系在什么地方,天的顶端置于何处。)北极星以下,沿地轴方向分为“九重天”,与天外的“辛天”共同组成十天干;而十二地支,则是将黄道面划为十二等分形成的分区。三种说法皆各有其理,尚需进一步考证。
至于一天分多少个时段,也是反复更易的。最初,华夏先民只将白昼设置了三个标识点:平旦(或日出)、日中、日入(或昏、夕)。后来扩展为六个标志点:旦、大采、中日、昃、小食、小采。至商朝又将一昼夜划分为12个时段,分别为:旦(日出)、大采(朝食)、大食(日中前)、中日(正午)、昃(日偏西)、小食(下午)、小采(傍晚)、暮(日入)、昏(黄昏)、夕(夜晚)、寤人(夜半)、昧辰(昧爽,黎明)等。但这12个时段并不是等长的,对白天的划分较为细密,夜晚则相对粗疏,当然,这符合农耕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规律。
《淮南子·天文训》中有“昼者阳之分……故分为十时”之言,这是将白天划分为十个时段的最早记载,这一方法又称“十政”或“十位”,即从日出到日落,参照太阳位置、天色变化或用餐活动等分为旦明、蚤食、晏食、禺中、正中、小还、餔时、大还、高舂、黄昏“十时”。《论语》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初义说的大概就是没到某个时段,就别考虑哪件事情。
《隋书·天文志》还记载了一种将昼夜均分为十段的制度,即昼为朝、禺、中、晡、夕,夜为甲、乙、丙、丁、戊(后用五更表示,每更又分五点)。大约至汉代,随着漏刻(也称漏壶)等仪具出现,人们不再完全依托太阳位置来定时,于是,我们熟知的将一昼夜均分为十二时辰的计时法自此创立。宋代以降,又把十二时辰中每个时辰平分为初时、正时两部分,这与我们今天使用的24小时制式已相差无二。
这里还有个疑问,与扶木、若木配套的建木作何使用?敞开脑洞猜测,如扶木、若木是替代日月出入之山作划分一年时段之用的,那么,建木的作用可能就是通过其“枝丫”观测太阳在天空中所处位置来确定一个白昼的时间,类似于“日上三竿”作为时间标志的做法。如果这个假想成立,则跟扶木在东、若木在西、建木在中的位置关系记述是相符的,也跟建木“日中无影”的描述相合。同样,如扶木、若木演化为测量季节变化的圭表,根据建木的日影变化规律衍生出测量一天时间的日晷也是可能的。于是,以日晷测正午,再固定于每天正午以圭表测日影,便能减少测量数据的误差。
四
关于华夏上古历法和计时系统的信息传递始终是混乱的,特别是时间线上的矛盾十分突出。由于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单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承续下来,其间必定存在讹化和神化的成分。加之后辈误读,或者将后世思想托古给先辈,以致造成原义的偏差甚至是颠覆,成为现代人迷惑的根源。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神话故事就是华夏历法演化史的暗线。其间有令人乱花迷眼的虚构叙事,也有客观存在的现实本源,因此,我们只能抽丝剥茧地,通过推测和猜想,去解构其内在关联和历史逻辑。
比如,“女娲补天”可能是将一年三百六十天增补到三百六十五天,而增补的这五天,被后世讹传为“五色石”,用于填补出现漏洞的天,从而赋予了这一事件浪漫的神话色彩。“夸父逐日”可能说的是观测太阳位置变化或者追逐日影变化规律,而改进了历法参照系统。“嫦娥奔月”或许是说常羲为制定阴阳合历,往复观测月相变化规律。“伏羲一画开天”是指将天文历法观测结果符号化、抽象化,实现从自然崇拜到宗教建构的精神跃迁。“羲和生十日”与“常羲生十二月”,也许说的是羲和制定了一年划分“十日”的历法,而常羲设置了阴阳合历,将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份……
还有“共工怒触不周山”,大概是说一位姓名不详的共工(主管水利建设方面的官员),在与颛顼争夺掌管天文历法的帝位时,因为度算失误,造成历法不能首尾相衔,因而羞愧、愤怒地撞断了自创的观测器具。故事中,“不周”是形容度量天文的历法不能形成闭环(如果推算准确则称为“周天”);“山”可以理解为一种演算天文历法的模型或器物。与此类似的说法,还有“不周风”,或指候风方法导致的历法失准。至于“不周山(风)”为何与西北方向相勾连,可能是因为通常在二十四节气图中,冬至是位于西北方向的,而冬至的推算精准与否,是关乎历法准确性的硬核指标,如若冬至日推算失准,历法自然“不周”。
最令人费解的,当数“后羿射日”(也有说大羿),对其内涵解读的争议也最大。关于“十日”一说,结合前面分析,可能是指在阴阳合历之前,先民曾创立的一套“十日历法”,即以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往复运动时,以山峰或者扶桑木标示出的十个位置作为标定点,用以指示季节的历法系统。由此推想,《山海经》里“一日在上,九日在下”的描述,大约指的便是在这十个时段中,太阳在达到北回归线前后这一时段,即夏至时分目测处于最高点,其余九个时段,处于较低位置,尤以冬至时最低;或者是一天当中,正午时分太阳处于最上方,其余九个时段处于下方。三星堆青铜神树大体也指向了这一说法,但从时间维度看,既然陶寺为都邑时已经出现圭表,那么至商代中晚期,以扶桑木测太阳位置定季节的方法恐早已淘汰,故此,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可能是为纪念“通天神器”扶桑木而经过美化的礼器(同样,三星堆文物外观特征上,已明显褪去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时期陶器上的“七间六衡、四时八节”等直观形象,而呈现出“回形纹”等经过美化的元素)。关于“射十日”则有多种解读,比如,有人认为“射”字通“设”字,“射十日”即设立了“十日历法”;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刘宗迪先生在其著作《失落的天书》里,提出“射十日”是向礼器上的十日“行射礼”;此外,还有一种可能,这个射字是指瞄准天空中某个目标的一种观测行为。这则神话的背景可能是由于历法失准,导致农作物生长周期失序,先民为正时序而创立了新的历法体系。至于故事里“射落九日”的说法,大概率是后人根据“一日在上,九日在下”的表述引发出九日被射落于地的附会。
总之,当您尝试着把这些看似杂乱无章、光怪陆离的神话传说剥离并串联起来,似乎就能发现,这些故事背后的内在逻辑是自洽并能够形成闭环的。
五
回顾华夏历法的演化史,至少经历过三次重大跃升。第一次是“绝地通天”,即脱离观察地面事物的物候历法,改为观天象以授时;第二次是“抽象为数”,即从具象的实物观测中推算出较为精准的数理规律,至此,华夏历法从单纯的农业指示工具演进为计时系统;第三次是“度数成器”,就是将反复演算的数理规律转化为计时器具的刻度。每一次改革,都是为了提升精确性和简便性,这便是历法演化的核心逻辑。
从中可以看到,华夏天文历法演化过程清晰、传承链条完整,是持续、独立演进的。加之从上古时代到元明时期,华夏以外地区的历法系统,直到如今也只能查到笼统的、碎片化的成果表述,看不清其演化脉络,难以作出关联性比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华夏历法体系具有高度的原生原创性,这一点,能够从多个维度交叉印证。
从文字维度看,天文历法是华夏文明的根基。汉字语境里“时间”二字包含时刻和时段两个概念,其中,“时”字上为表示景柱的“止”,下为代表天文周期的“日”,描述了将自然事物周期进行划分和标记的行为;而“间”字则表示这种行为产生的刻度之间的段落。又如,“度”“分”两字在甲骨文里均是从表示计量、测算的动词,演化为指示弧度、时长的量词。再有,甲骨文“中”字,似为观测日影和候风的形象;“华”字,像一尊扶桑神树;“东”字,像太阳升于树后(或为扶桑木);“龙”字大约源于龙星七宿的形象;“凤”字像一具粘着羽毛用来测风向的风信器。这些都与“在天成象,观象授时”的天文历法观测活动有关。
从权力视角看,授时权是古代最神秘、最威严的权力之一,其起源于对自然四时的原始崇拜,落脚于准确指导农耕生产。先民所尊“三皇五帝”虽有多个版本,但“三皇”都是为中华民族繁衍起到至关重要之人,而“五帝”则均为历法制定的主导者,“皇帝”之谓大约由此而来。周代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必是有依托天象而授时的使命。历代君王被尊为“真龙”,也定与观苍龙七宿而定时有关。这种神圣的权力,甚至与北极星同辉。
正因如此,周代以降,朝廷一直设有天文历法机构,并设专职官员。先秦至汉初设太史寮,为最早的综合性机构,兼管天文、历法、史书编撰。汉设太史令,隶属太常寺,负责天文观测、历法修订,其负责人也称太史令;东汉加设灵台丞负责具体观测。魏晋南北朝设太史局,由太史令、太史丞负责。隋至唐初设太史局,武周时改制司天台,官员为太史监(监正)、司天少监(监副),工作人员有:保章正(负责星象观测与记录)、灵台郎(管理天文仪器)、挈壶正(掌管计时仪器)。宋元时期,北宋设司天监,后改称太史局,官员有:监正(宋)、太史令(元),少监,春官正、夏官正(分掌四季星历),并设天文生等基层观测人员。明清时期设钦天监,官员有:监正,监副,五官正(春官、夏官、中官、秋官、冬官),天文科博士(负责星象观测),漏刻科博士(掌管时间测量)。
同时,华夏天文学家也人才辈出,比如战国的甘德、石申夫,西汉落下闳,东汉张衡、刘洪,南北朝祖冲之,隋代刘焯,唐代袁天罡、李淳风、一行,宋代苏颂、杨忠辅,元代郭守敬、王恂,明代邢云路,清代梅文鼎……一串串响亮的名字,撑起华夏天文历法的穹顶。

阆中市锦屏山观星楼前落下闳观星塑像(图源:阆苑仙葩阆中古城景区微信公众号)
由于历法失准、不合天象、日月食预测有误等诸多原因,以及对历法的不断修正和精度提升,中国历史上创造并正式使用的历法超过百部(清代学者汪曰桢《历代长术考》统计达115种),其中被官方正式颁行或产生重要影响的约有53部。从早初的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统称“古六历”),到汉代《四分历》、刘歆《三统历》,再到东汉刘洪《乾象历》等,精度逐步提升。比如《乾象历》提出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两值偏大的问题,并确立了近点月概念和它的长度计算方法。东晋虞喜首先发现太阳运转到冬至点的位置每年并不相同,将其定义为“岁差”。祖冲之最先把岁差应用于历法的制定,他所制定的《大明历》将一年定为365.2428148日,仅比现代测定值相差46秒。
后隋朝刘焯根据日行盈缩的规律,创立盈缩躔差法,制定《皇极历》,测定岁差为75年差1度,与现代测定的76年差1度的准确值非常接近。唐代僧人一行在《大衍历》中提出“日有盈缩”这一重要发现。南宋杨忠辅主持修成的《统天历》测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元代郭守敬主持设立27个观察台、站,测量日影和北极极地高度,以及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昼夜日刻的测定,修成《授时历》,成为中国古代最精确和使用时间最久的一部历法。明代邢云路虽没有进入钦天监,但其算得回归年长度值为365.24219日的新值,与理论值之差仅约2秒,为《崇祯历书》的制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华夏历法对岁首(即一年之始)的定义同样历经演变。其中,夏朝以寅月(农历正月)为岁首,称为“夏正”。商朝将岁首提前至丑月(农历十二月),称为“殷正”。 周朝再提前至子月(农历十一月),称“周正”。秦至汉初沿用颛顼历,以亥月(今农历十月)为岁首。至汉武帝时期,由落下闳为主提出,恢复夏正(农历正月)为岁首,这便是现在春节的源头。
不同时代对于一年的称谓也并不一致。唐虞称一年为“一载”;夏朝称为“一岁”。殷商至西周时期的部分诸侯国,称一年为“一春秋”,即以收获的季节为标准,把一年分为“禾季”与“麦季”。商王把一年称为“一祀”,将祭祀作为最重大的事务。到了周代,才称为“一年”。
伴生于天文历法的数学著作不胜枚举。唐代李淳风编纂的《算经十书》,收录了涵盖汉至唐初的十部数学典籍,包括西汉《周髀算经》、东汉《九章算术》、三国《海岛算经》、南北朝《孙子算经》《缀术》、北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唐代《缉古算经》、北周《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等,展示了华夏天文历算成就。宋元时期,《数书九章》《四元玉鉴》等将中国古代数学推向一个高峰。
还有观测器具,也是层出不穷。比如先秦时期的候风仪、圆规与矩尺、扶木与若木、通天柱、圭表,汉代的日晷、浑仪、天球仪,宋元简仪、仰仪,明清象限仪、六分仪等。以及专事计时的汉代刻漏,宋代水运仪象台,元代的大明殿灯漏等,无不体现古人智慧。
至此,华夏天文历法至高而止,但其对后世的启示和影响不容遗忘。
六
当历法用于指导农业生产的地位逐渐弱化,其计时功用开始随着社会需求的提升而逐步显现,计时器具也不断被发明,并持续精进。
1283年,英格兰贝德福郡的丹斯塔布修道院安装了历史上第一座以砝码(重锤)驱动的机械钟。1335年,意大利米兰等地出现公共机械钟,首次实现整点自动打点报时,标志着机械钟进入城市日常生活。15世纪初,德国钟匠彼得·亨莱因等人用钢制发条替代重锤动力,制造出小型便携钟表,为家用钟和怀表奠定基础。约1450年,均力圆锥轮的发明解决了发条松紧导致的走时误差问题,显著提升便携钟表的精度。1564年,德国纽伦堡诞生首只怀表“纽伦堡蛋”,采用发条驱动和机轴擒纵机构,但当时仅有一根时针。1656年,荷兰科学家惠更斯应用伽利略摆锤理论,设计出首台摆钟,将日误差从15分钟降至1分钟以内。1675年,惠更斯又发明游丝摆轮系统,取代钟摆用于便携时计,推动怀表精度飞跃。这便是机械钟表登上历史舞台的进程。
此外,1582年,世界天文历法史上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格里高利历启用。这是现代公历的源代码,也是后来建立世界统一授时权的本底。这一年10月,部分欧洲国家的历法里少了10天,即10月4日后一天直接跳到10月15日,这是此前使用的儒略历累积误差没有修正造成的。此后,世界各地大多数国家逐步统一使用格里高利历。这当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884年,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设置了本初子午线,成为世界标准时间的基准点,也是授时权在全球范围内的集中统一。在这部历法中,计量单位“月”(month)不再与月亮(Moon)直观的月相变化有勾连,而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单位。
由于现代科技发展,对高分辨率计时的需求越来越高,时间计量手段也越来越精细。1927 年,沃伦·玛丽森和约瑟夫·霍顿在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研制第一台石英钟。在这些装置中,电流使石英晶体以远高于摆钟振荡频率的某个特定频率共振,从而实现更高精度的计时。但它们也必须用地球的自转周期进行校准,由此,“一秒”被定义为平太阳日的1/86400。
1955年,路易斯·埃森和杰克·帕里研制出第一个实用的铯原子频标,从而启动了计时领域的革命。在1967年的国际计量大会上决定,人们将“秒”重新定义为“铯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之间跃迁所对应辐射的9192631770个周期”。
至此,时间的计量脱离自然界的参照标尺,并逐步减少人为设定,改为依赖于有规则振荡周期的自然现象。而现代天文学也不再是为历法提供标定点的学科,因此,毋宁称其为“天体学”恐更为准确。同时,现代科技提升的只是计时的精度,单纯从历法系统而言,明代就已达到精度的天花板,甚至比现行公历还要精确,只是这微小的差异,对现实生活的影响甚微。
自17世纪初王徵仿制欧洲自鸣钟起,中国人也在紧跟世界计时系统先进科技,古老的历法思想,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总之,从物候历到铯原子钟,人类对时间的精准需求助推了测量手段与细分能力的提升,但回过头看历法与计时系统精进的历程,仍依稀可见坑洼的来路以及道路上散乱的履痕。这大约就是智慧型碳基生命的情怀所在。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黄 森(威远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供稿:威远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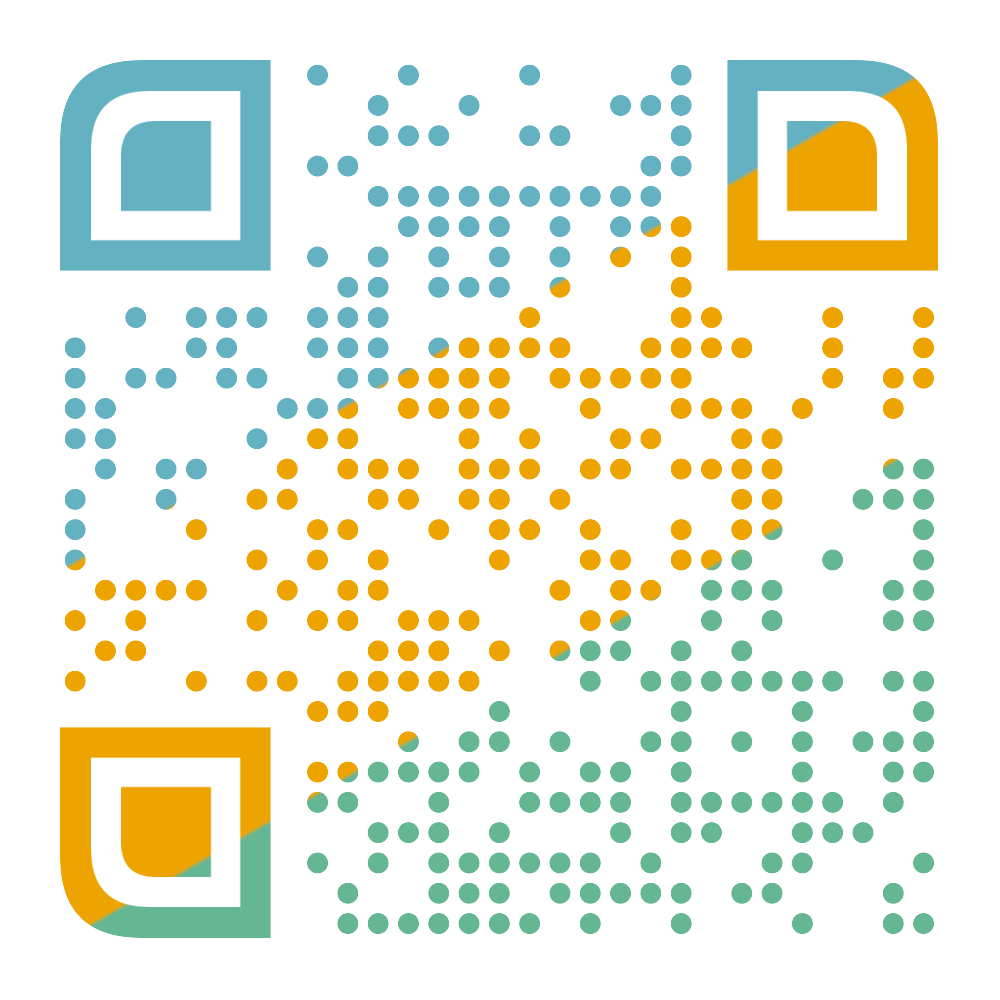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